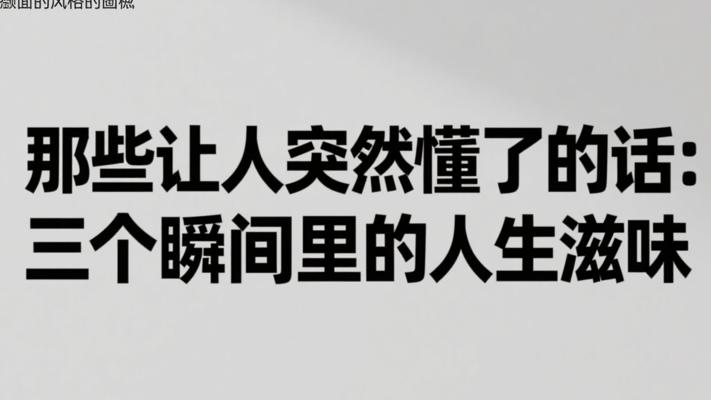
内容预览
【那些让人突然懂了的话:三个瞬间里的人生滋味】去年收拾旧相册时,翻到张泛黄的工作照,突然想起老周说的那句话。那是我参加工作第一年,在西北戈壁的泵站认识的同事老周,他总爱眯着眼讲当兵时的事。
"在内蒙古放羊那会啊,"老周往搪瓷杯里续着热茶,水汽氤氲中他眼角的皱纹堆成褶子,"早上卡车把我们和羊群扔到牧场,放眼望去全是草,一直长到天边上。"他顿了顿,指尖敲了敲杯子沿:"有次我盯着天看久了,突然觉得害怕——天太大了,不敢去望。"
当时我正啃着硬馒头,听见这话差点噎着。后来才慢慢懂了他的意思。有次出差路过草原,我特意下车站了好久:清晨的露水还挂在草叶上,羊群像撒在绿绸缎上的白芝麻,可一抬头,蓝得发慌的天像口倒扣的大锅,把人严严实实扣在底下。风一吹,草浪从脚边滚到天边,突然就明白老周说的"不敢望"——天地在草原上毫无保留地铺展开,让人觉得自己渺小得像粒沙子,连站在哪儿都显得多余。那一刻才懂,原来真正的辽阔会让人害怕,怕自己被这无边无际的天地吞掉。
前年暑假,老家侄女月月来城里玩。送她上绿皮火车时,这丫头扒着车窗直兴奋,小脸蛋贴着玻璃看不够。等火车哐当启动,她突然扭过头,眼睛瞪得溜圆:"叔叔你看!这火车真有意思——人对着人坐!"
车厢里先是静了两秒,接着哄笑起来。我旁边的大姐笑得直拍大腿,月月却被笑得不好意思,往座位里缩了缩。可我看着她攥着座位布的小手,突然笑不出来。这丫头长这么大,第一次走出山沟,在她眼里,火车最稀奇的不是轰隆响的车轮,而是面对面的座位。想起上次去她家,她趴在土炕上用树枝算算术,窗外是连绵的山;现在她坐在晃荡的车厢里,对面坐着陌生的城里人,手里紧紧攥着我给她买的面包。
后来每次坐火车,看见对面座位的人掏出泡面或者看手机,我就想起月月的话。城里孩子觉得理所当然的事,在乡下孩子眼里却是新鲜风景。有次跟朋友聊起这事,他说:"你侄女那句话啊